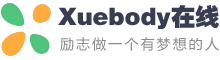致读者
纷纷占据我们的灵魂,折磨我们的肉体,
犹如乞丐养活它们身上的虱子,我们居然哺育我们可爱的悔恨。
我们的罪孽顽固不化,我们的悔恨软弱无力;
我们居然为自己的供词开出昂贵的价目,我们居然破涕为笑,眉飞色舞地折回泥泞的道路,
自以为用廉价的眼泪就能洗去我们所有的污迹。在恶的枕头上,正是三倍厉害的撒旦久久地摇得我们的灵魂走向麻木,
我们的意志如同价值连城的金属被这个神通广大的化学师全然化为轻烟。
正是这个恶魔牵着支配我们一切活动的线!
我们居然甘受令人厌恶的外界的诱惑;每天,我们都逐步向地狱堕落,
穿过臭不可闻的黑暗也毫不心惊胆战。仿佛倾家荡产的浪子狂吻狂吸丰韵犹存的妓女那受尽摧残的乳房,
我们居然一路上偷尝不可告人的幽欢,竭力榨取幸福,像挤榨干瘪的橘子。
宛如无数蠕虫,一群恶魔
聚集在我们的头脑里,挤来挤去,喝得酩酊大醉,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死神每每潜入我们的肺里,
发出低沉的呻吟,仿佛无形的大河。倘若凶杀、放火、投毒、强奸还没有用它们那可笑的素描
点缀我们可怜的命运这平庸的画稿,唉!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不够胆大。
然而,就在我们的罪恶这污秽不堪的动物园
所有正在低吠、尖叫、狂嗥、乱爬的豺狼、虎豹、坐山雕、
母猎狗、蛇蝎、猴子和各种怪物之间,却有一头野兽更丑陋、更狠毒、更卑劣!虽然它并不凶相毕露,也不大叫大喊,
但它却处心积虑地要使人间沦为一片断壁颓垣,即使打哈欠也想吞没整个世界;
这就是“厌倦” !——眼里不由自主地满含泪水,
它抽起水烟筒,对断头台居然浮想联翩。
啊,读者,你对这不好对付的怪物早已司空见惯,——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我的同类!
张秋红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