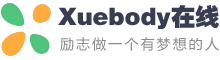世纪的前夜
在屋角街头的拐角
历史正遭到抢劫
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
看不见灯光
是时候了
多少年来
我提心吊胆
唯恐错过永恒
是时候了
死亡,使这一瞬间
成为紧要关头
而此时我坐在屋子里
反反复复推敲自己
像推敲一个
来历不明的字眼
也许是时候了
我看见天堂的字迹
辉煌的一闪
看见那只血淋淋的断手
把这些燃烧的字迹
涂抹在一堵墙上
于是,我相信
我就是那个人
那制止暴行的人
那历史监护权的合法继承者
长着一副临终的面孔
为这副面孔需要拿出勇气
需要摆好架势
走出由昏黄的灯光
和日常琐碎的动作
构成的低矮的空间
进入夜晚
去宣布一次拒绝
以便获得一次
盛大的火刑仪式
我仿佛看见
枪口正对准我的脑袋
听见子弹穿透思想
发出沉闷的碎裂声
看见我的脸上挂着
从那些伟大死者的嘴角
剥下来的干燥的笑容
戏剧性地进入了永恒
可我又怎能忘记
这些过了时的举动
很难再次引起
预期的轰动
殉道者的荆冠早已破破烂烂
被塞到了床下
他们已经死了
这些历史的监护人
曾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站着
不能入睡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失去了警惕
一切都得到了默许
剩下的是些伪先知
是些荒原上的布道者
他们翻披着褴褛的灵魂
出没于人群麋集的街头巷尾
叫卖无人问津的天堂指南
并在贫瘠的头盖骨上
不厌其烦地播下那些
发霉的字眼
徒劳无益地等待收获
他们只得隐姓埋名
战战兢兢
担心被认出
担心被送进疯人院
他们全都错过了永恒
可我该怎么办
或者我仅仅是活着仅仅是
那些被死亡反复咀嚼又吐出的
失去了滋味的人们中的一个
如果真是这样
我又何必掩饰我的怯懦
当历史遭到抢劫的时候
我怎能证明我不在场
怎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又怎能证明
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屋子里
无害地推敲字眼
没有紧要关头
没有永恒
什么也没有发生
有的只是字眼字眼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