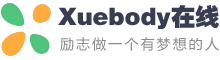射手
弓的名字是生,它所作的工却是死。
――赫拉克利特
历史的这一页已经残缺不全,
但这个背影特别之处,在于一把弯弓。
当他射向野兽,他被称为猎人,
否则,就一脚踢开他冷僻的本名
养由基,径直叫作射手。
和平年代,他的目标是
漫无目标的天空,
他的大笑摆设了深山的豪爽。
他用生命的狂喜扩张一束马尾,
用黑暗的箭杆触碰黎明之光。
当我将这一页轻轻翻过,
谁也不能阻止我成为我诗中的射手,
谁也不能阻止我来自多刺的楚国。
我来了,随一队楚军在河南与晋国交手。
那是公元前575年,
当我的王的眼睛被晋国人射瞎后,
我受命还击,但我的手中连同我自己
也只有生和死两支箭矢。
我面无表情,象一个烧透了的秦俑,
第一箭就将那人当场射死,
接着又射一箭,把他射活。
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