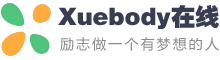我是比利时章平,你也是的
我是比利时章平。你也是的
摇起身子,一起吹了萨克斯
且是一支铜管跑出两种声调
徘徊窗外的,象这个雪夜
象你所说“心不能如雪融落水里------”
风雪没有针线,你说不必缝补
在这个冬夜,你不握一下手就走
离开我,如渐渐走入眼前镜子
只是,依旧翘了蓬松头发
烫疤烫的脸颊,我找到一撮山羊胡子
我和你是一个人,我和你是两个人
我和你的熟悉,比别人更不熟悉
偏偏在这里,同时租用身体
我和你发动了一个人的战争
没法退出,又喜欢互相射击
我在雪夜,用萨克斯诉说无奈
你不喜欢的忧郁。你说痛恨矫情
又不同情人的苦恼,对我毫不理睬
让我象床底旧鞋,独自充满落魄
窗外的风雪很大,你走得很急
你很在意,对我的一些错失
哪怕应该忘掉,你还唠叨不绝
恰如今夜突然想到的一个道歉
因了这个朋友死去,已经太迟
你出走,丢下我,独自怄气
我也想把自己弄得象样一些
做事果断,对人热情,别太自私
结果是,醒来无法改变事实
对金钱谨慎保存,对别人小心提防
上街买菜,斤斤计较,还脸红耳赤
我是比利时章平。你也是的
象这一首诗,但改自另一首诗
象走过雪地,身后继续落雪
雪复盖了道路,象复盖去的脚印
让人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