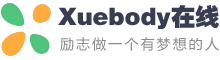种烟叶的女人
你在床和窗子之间
种子许多烟叶
(用水泥地板种出来的)
那种烟叶
又香又嫩
你一早出门去
抽着这种烟叶
我做饭时
也能闻到
那时
表明你要回家了
我手上的动作就更快
有时候
我也偷偷吸两口
(我太累了)
绕着那小块烟叶地走两圈
每次总是又舒服又习惯
除了种烟叶
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知道在什么时候
打开窗子
通通风
想着你在一个什么地方
和别的女人们吸烟
并且谈论我的作坊
我感到很快活
我私下里打算
翻过年去换个地方
老种这种烟叶
也够腻味的
当然,在你面前
我还是很规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