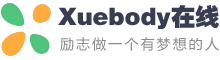乡归
奥德修斯回来了,回到溪谷边的农场
那里冬青丛围护的房屋
饱藏着时间的遗迹——他那些人鬼莫辨、
发黄的照片;挂钟的计量
人生的指针;信守婚誓的母亲,悲苦
如珀涅罗珀。窗口海风声欢。
比特洛伊更长久可怕的围困
重开战幕。凌驾一切的爱
无病呻吟,幽黑似海,毫无内容:
爱的不毛之地曾哺育他儿时的自由之梦,
也曾使他沉醉在喀耳刻的大厅,归来
他又得到爱,这对他更加残酷难忍。
她没有说“你变了”;也想象不到
他们循环往复的生活不仅是静静
流动的漩涡。可她仍然希望
将他包进襁褓,搂在怀抱
放入最初的樊笼,摆脱种种野蛮的生活之争。
他永不结婚——她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她将替他烧水做饭,跟他唠叨南方的气候
怎样伤她关节。而他——反抗,又屈服于
古老的誓约——抚慰那生产的阵痛中
哀叫的母羊。皮鞍的味,或集日的酒
是他的天地;他隔着稀疏的田野他仍听到远处
大海的六音步韵律拍打着礁石和岩洞。
陈时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