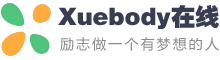一
我的歌高于天山,
胜过一切晚宴。
我的路愉悦了躬耕之犁,
田野中擦亮,闲暇时发光。
纵然我的手伤心,
分成悲哀的五,
我的刀却正值盛年,
是犀牛永生的角,
在哪里逗留,就在哪里闪烁。
我是“唯一”之神,沿荒年行进。
我常著愤怒的衣饰,
以恐怖束腰。
二
我的话就是北风,
即使落在地上。
我的唇极其美好,
我的额自黎明就与太阳同车。
我的城正如我的话
永不丢失,
十万大山是它一切传言的基础。
我飞翔,我明亮,
明歌自我的口中流出,
所以它的名也有翅膀。
我飞翔如渡鸦之羽在阳光以上。
三
巴比伦的神,埃安娜,愿她永生!
一切时间都已离开,
因有关她的谈论已经兴起。
我的手保护,在万军之上。
在我意愿的北端,
大树已向我仆倒。
一切殿堂在我离开之日都步入老年,
我的心确是双刃的剑。
我将在秋天与她相遇,
正如丰收和美酒。
我魅力的深渊对她说话;
她倾听,她的心顿时种上兰花。
四
双腿啊,你传言的绿洲使眼睛明亮。
在我沿着旷野的基础
改换国家的时候,
我前方的路必用缎子铺成。
我的眼就是圣经的两页,
就是从香草弥漫中派生的一对黄莺。
我的歌使白云变黑,
并引导了大雨。
双腿啊,你行进如响雷
在“昌盛”的两岸。
一切与你为敌的,必是悲哀之旅。
五
我的欢笑就是猎鹰
回到“快乐”之巢,
因我亲见它们。
那寻找我的,必寻不见;
与我只有一条翅膀的距离,
却不能看到。
当黑暗包围了兰花,
智慧也回归了我的四野。
我给了他们登临的杖,并建立了群山。
它们超过了会众的双眼,
除了大海,无人将它度量。
我的心确是刻有铭文的,
确是一切往事的许可者。
我的话仅为深水打开辨认之窗。
我的每个字都是狐鸣,
招来了乌鸦之羽,
像交错的大殿,接合的檐角。
我使一切礼赞在自己手中,
因我剩下的勇气仍可伏虎。
永不留下,也不忧愁。
我确是一阵晚风疾行,
去见那聆听者。
他们细听;他们萦绕了我
和我因回顾而展现的孤独。
六
在北堂我种植忘忧的萱草。
我的心是豪迈的黄杨树
所喂养的褐色野鸭。
我把行进之风穿在自己脚上,
以远途巩固了生命,
安顿了衰微的旷野之马。
当天阶上的守望者一一到来,
以造就天堂的砖石压低了云彩,
请用这杯瓴留下这雨水,
因为我新死,
与众神相争。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