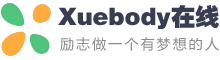她的丈夫
呆呆地回家来,一身煤灰,蓄意
要把洗脸池弄脏,毛巾弄黑,
要她靠板刷和搓衣板
来懂得钱的顽固性格。
要她明白他是从什么样的尘土中
得来他的干渴和止渴的权利,
他流了多少臭钱换来这点钱,
这点血汗钱。他要她受点委屈
明白她有新的义务要尽。
木屑似的炸土豆片,放在炉子里保温了两
个小时,
不过是她回答的一部分。
他还听说了些别的,就把土豆片扔回炉子,
走到房子那一头去了,唱着
《重归索伦托》②,嗓音
象响亮的烂铁片,
她的背鼓起来成了驼峰—— 一种侮辱。
他们都想得到自己的权利
他们的陪审员得从
小小的煤灰上召集。
他们的辩护状直接送上天,再不见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