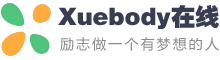慕尼黑女模特
完美得令人敬畏,但不能生育。
冷酷如雪的呼吸,填塞了源泉。
生命的树,生命的树。 一个月又一个月,空虚放逐她们的月光。
血液的洪水就是爱情的泛滥。 上帝的牺牲品。
它意味着除了我没有更多偶像, 我和你。
在她们漂亮的硫磺和笑容里 这些女模特儿委身在今夜的慕尼黑
陈尸所就设在巴黎和罗马间, 她们不加掩饰地裸露在皮毛里,
桔子吊在银色的枝条上。 无可容忍,失去了灵魂。
白雪撒下黑色的花瓣。 四周没有人迹。在繁多的旅馆里
一双双手在把门打开,放下鞋子 为了一盒鞋油走进这里
肥硕的脚板将在天明消失。 哦,这些窗孔中的家庭生活,
婴儿的鞋带,有绿叶的糖果, 密集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圣带里昏昏欲睡。
黑色的耳机在手指上 闪烁着华丽夺目的光芒
它在闪烁、融化 沉默,雪落无声。 赵琼 岛子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