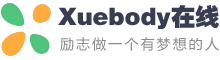神秘论者
天空是镰刀的磨坊──
无法解答的问题,
闪烁,醺醉如飞蝇不堪忍受的叮吻
在夏季松下的夜空发臭的子宫里。我记起木屋上太阳腐朽的气味,
撑紧的风帆,狭长咸湿的裹尸布。人们一旦见到了神,还有何补救之道?
一旦陷入困顿没有一部份残存,没有一根脚趾,一根手指,而且耗尽
完全耗尽了,在烈阳的炙烧中,在自古代教堂延伸至今的污点里,
还有什么补救之道?圣餐上的锭剂,死水边的漫步?记忆?
或在啮齿动物之前,拾取基督明亮的断片,
温驯的食花者,他们希望低微易于满足──驼子在她矮小洁净的茅屋里
在铁线莲的轮辐底下。难道只有温和,就没有伟大的爱?
大海可还记得行经其上的人?意义自分子间滑落。
城市的烟囱呼吸着,窗门淌着汗,孩童在卧床上跳跃。
太阳盛开,这是天竺葵。心脏尚未停摆。张芬龄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