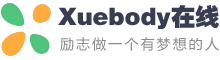我爱你,腐坏者,
美味的腐败。
我喜爱把你从皮里吮吸出来,
这般的褐色,如此的柔嫩、温和,
如意大利人所说:病态的细腻。
多么稀奇、强大,值得追怀的滋味
在你堕入腐烂的阶段中流溢出来,
如溪水一般流溢。
芬芳扑鼻,像西那库斯的葡萄酒,
或普通的马沙拉。
尽管马沙拉一词在禁酒的西方
将很快带有矫揉造作的意味。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在转变为葡萄干的葡萄里面?
在枇杷、山梨里面?
褐色病态的纵饮者,
秋天的排泄!
这是什么,它使我们想起白色的神明。
上帝一丝不挂,像去皮的桃仁,
奇特,不太吉祥的果肉芳香,
仿佛渗了汗水,
并且浸泡了神秘。
顶端枯死的山梨和枇杷。
我说,恶魔般的体验非常美好,
似俄耳甫斯的音乐,像下界的
优美的狄俄尼索斯。
离别时分的一记亲吻,一阵痉挛,破裂时分的一股兴奋,
然后独自行走在潮湿的道路,直至下一个拐弯。
那儿,一名新的伴侣,一次新的离别,一次新的一分为二,
一种新的对离群索居的渴望,
对寂然孤独的新的心醉神迷,处在那衰弱的寒叶之间。
沿着奇异的地狱之路行走,越发孤寂,
心中的力量逐一地离去,
然而灵魂在继续,赤着足,更生动地具体表现出来,
像火焰般被吹得越来越白
在更深更深的黑暗之中,
分离而更加优美,更加精炼。
所以,在枇杷与山梨的奇特的蒸馏中
炼出了地狱的精髓。
剧烈的离别的气味。
一路平安!
俄耳甫斯,蜿蜒的、被树叶阻塞的、寂静的地狱之路。
每颗灵魂与自己的孤寂告别,
最奇特的伴侣,
最好的伴侣。
枇杷、山梨,
更多的秋天的甜蜜流动
从你空洞的皮囊中
吮吸出来
啜饮下去,也许,像呷一口马沙拉,
好让蔓延的、自天而降的葡萄向你增添滋味,
俄耳甫斯的辞别,辞别,辞别,
狄俄尼索斯的自我总和,
完美的陶醉中的自我,
最终孤寂的心醉神迷。
吴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