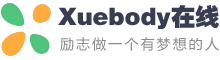天黑了
每条嘁嘁喳喳的小巷都睡了
末班车也已开出
他还没躺下
闹钟嗑着时间,嗑着他
许多人传说
他老了
他是开始变得象琥珀
象那片秋天里深红的夕阳
象从大海心脏游上岸的一朵浪花
他琢磨出数不清的雨花石
他曾是春天里的桑蚕
可他的青年时代遭遇了梅雨季节
留给他的只有花了的眼睛
和斑斓的白发
他离不开拐杖了
怎么能象比春天更明媚的姑娘和小伙子
二十五岁时,他晚婚
没想到一晚就是二十四年
四十九岁
他结婚……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添了一个人,又添了一个
依然只能听到“沙沙沙”的笔声
他规定每天只和妻子谈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温柔体贴的话
他很爱她
妻子等着丈夫
孩子等着爸爸
读者等着诗
他自己呢?
他说:“年轻不能以年龄计算
应该以心灵……”
他老吗
他的笔象他的血管一样
颤抖着但依然流淌着
他拄着拐杖和孩子们去公园坐木马
年轻人要他回忆童年,他又糊了一只风筝
他的诗也是一块琥珀
他海一样背着太阳跑着,跑着
脸晒得那么黑
你看他秋天般笑着
你看他那时间一样的步伐
那满头雪一样白发
……
今天,是青年的节日
过节,一大早大家就跑开了
象孩子一样叠了一排纸船
放它在脸盆里航行
吹一群五颜六色的气球挂满屋顶
又唱起了那支唱不好的歌
真的,我们过节
空气里挤满了欢声笑语
门和窗口开放着笑脸
阳光为我们张灯结彩
心里话瀑布一样奔腾直泄
突然发觉
样子比爸爸还显得老
真不该老低头背单词
一个人躲进黑影里抽烟
我们有无边无际的希望的原野
有没被踩过的透明的天空和一条彩虹
有一条忠诚的小路和自行车
我们过节,真的
把太阳戴在头上
把月亮留在宿舍
把你和我摄进一张彩色照片
不让她们再走
举起啤酒杯什么也说不出
晶莹的脸蛋红了一片,又红了一片
过去和未来的结晶从眼睛淌了出来
真高兴呵
这个夜晚,今天属于我们
我们是青年
今天我们过节
……
谁都没想到
等了五年的车,天天一起挤却没说过一句话
有一天是可能的
那天下雨,你举着花伞,我站在伞中
我望你一直到终点,你一直看着雨
目光始终被一股说不清的感觉打断
顺着雨珠落下,无声地流向马路边
很久很久我在生气
终于有一天,一个小伙子送你,手勾着你的胳膊
你象看表一样看他,什么也没说
穿着五彩缤纷的连衣裙好象等的也不是车子
我远远躲在嘈杂背后,不知在想什么
后来好久见不着你
后来你来了。变了。怀里多了一个吃奶的孩子
后来一直是你抱这孩子挤这车
上车下车,挂钟的钟摆一般
谁都没有注意
有一双眼睛象启明星一样等待过你乌黑的眸子一闪
你似乎也不知道
象那次看表一样看着我,看着人群
看着孩子
看着纷纷飘落的雪花
……
……
每天每天的清晨
校园里有线广播都传出嘹亮的歌声
同学们先后从床上起来
可鲜红的太阳常常还没有
在挂满霜花的玻璃上出现
一个接一个背起书包
为听那堂讲不完的神话
为心中那个四季一般的情不自禁的信念
向那条钢筋水泥混凝的道路
向固定的教室
向寂静的图书馆
天快黑了,又匆匆忙忙去打水买饭
他距离每条道路都很近很近
但每条路距离成功都很远很远
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
他不敢
他不敢跟拄拐杖和戴花镜的老年人讲道理
年轻是他唯一的资本
也是他最难克服的缺点
公共汽车上他很少有机会坐坐
他把位置让给了形形色色抢座位的乘客
让给了游人大大小小的旅行袋
人们习惯了他把方便让给任何一个人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因为他有的是时间
他是一个青年
他没有自己的房间
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
没有自行车
甚至还没有一位给他写信的女朋友
他只有挺少一些助学金
没有资格,缺少时间,缺少钱
“他是一个青年”
每本谈论青年的书里
都这样语重心长地写着
人类无数空白历史和现实要求他填
现代化一道道命题科学逼他计算
还有墙一样的古籍读者等着标点
一个青年,二十几岁
将来要帮助父亲,也要做父亲
还要澄清混浊了千百年的黄河
沿着原稿纸标准的方格子他走呵走
一行又一行,一遍又一遍
可是,无论星星和太阳
无论日光灯和窗户
都经常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他始终迷信星星和太阳,迷信火山
迷信童年的纸船
在烤人的太阳光
在微弱的蜡烛和路灯下
在宁静得无声无息的日光灯下
他春蚕吐丝一样吐着
路一样不屈不挠一直向前
把希望交给透明的双眼,交给血管
交给砂轮一样一分一秒的时间
天天在微薄的饭菜票中节攒
天天熬到深夜一点
天天规规矩矩排队
天天在每双朦胧的眼睛寻找
热烈的太阳和纯洁的海水
天天在日记里思考和设计联系手与手
心与心、今天和明天的桥梁
征服距离走出太阳系的火箭
天天吸含尼古丁很高的“飞马牌”香烟
宿舍挤,食堂和图书馆挤,车站也挤
没关系,挤有挤的优点
挤,温暖
食堂里的面包怎么又小了
怎么能干的小伙子和纯洁的姑娘
还偶尔无可奈何地失恋
不要紧,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我们向前看
没说,什么都没说
火山一样默默地孕育着,孕育着
什么也没说
今夜属于他,明天也属于他呵
因为他是一个青年
……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借口
就是想去坐坐
那天大家说了很多、很多
尤其那位玻璃似的女同学
平时她象一股羞涩的风
匆匆地一闪而过
那天却象仲夏的雷阵雨
“哗啦啦、哗啦啦”一直下着
开始我们议论黑格尔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来扯到“飞碟”一般的世界
最后终于谈到
一种种别扭又时时都有的感觉
紧张严肃,却不团结活泼的
学习和工作
底菜一样的周末
形形色色的人的性格
萨特和弗洛依德
我们感觉有一大堆的为什么
那迎风飘摆的长裙和瀑布似的长发
不是女同学的美吗
怎么却象红色信号灯
男同学见了就躲
不然大家就要议论他有点那个……
不是吗
我们常常一样夜不能寐
一样常常躲进潮乎乎的盥洗室
把烦恼发泄到脏衣服上
一样忘不了对照巴掌大的小镜子
和路旁的一块块玻璃窗户
不放过自己一根被风吹乱的头发
也常常一样在深夜散步
希望和等着……
可一天又一天,一瞬又一瞬
碰到的一刻
不是目光回避
就是擦肩而过
我们有一双双明亮的眼晴
需要注视和认识所有的眼睛
和跟眼睛一样的一切
我们能看透一本本线装的历史书
能注释《小逻辑》
怎么就识不破一个抽象的性别
等什么?怕什么呢
又有什么不能理解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去了,真的,下一周我们还要去,那天
眼睛里升起一轮太阳
爬满喇叭花的窗外
荡漾起一支光芒四射的歌,真的
即便没有苏小明
没有《大众电影》《大篷车》
我们也不会感觉时间象个包袱
把心消磨在香烟和梦里
我们不在象一片空白似的
那样单纯的纯洁
我们开始珍惜每一分钟
热爱这五彩缤纷的集体生活
因为它不再是一、两本书
二十几节课
朦朦胧胧地跟着读
背诵和默写
……
在一声沉重的叹息里
晚潮
把木船托上海滩
老人的心
补缀着失败记忆的心
不再为希望张开
布帆凋落下来
象深秋最后的一片叶子
桅杆上
挂着一个光秃秃的冬天
从沙滩上出走
又从沙滩上归来
深深浅浅的脚印
穿过渔港上空的喧闹
穿过怜悯和哂笑
记录着
老人留给世界的遗言
躺在木屋的阴影里
老人整日整日地眺望潮汐
鲸鱼的白骨和红鬃的雄狮
在潮汐上
跳动着结局和追求
现实和梦 泪水
带着海的苦咸
顺着老人眼角的皱折
顺着一道道人生的经历
浸湿了深藏的故事和骄傲
但是 失望的英雄呵
请相信我
你没有被打败 虽然
桨和舵柄折断了
浮动在漩涡冷笑的唇边
被海风到处讲诉
虽然垂死的鲨鱼
带走了刀和鱼叉
带走了战胜厄运的可能
失败却并不属于你
白骨和雄狮
拓开了海平线那边的世界
在每天每天
被沙丁鱼般的赞美与收获
在疲惫不堪的孩子们心上
编织着海那边的神往
老人呀老人
我就是那个
老是被妈妈监护着的孩子
海流 沙丁鱼和鲨鱼的牙齿
都不能留住我的神住
请带我一同出海吧
我要到
海的那一边去……
……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隧道与空谷之间
车窗刚透出久逝的蔚蓝
阳光刚扫过记忆底层的灰暗
被黑暗切断的日光 刚刚结痂愈合
掀动窗幔的天风 刚刚把绿色的微笑
卷进每个旅客的心坎
从所有的车窗
所有躲藏着夜晚的地方围拢过来
隧洞的巨口
吞没了站牌 野花 环抱村镇的溪涧
吞没了车窗框成的山水图
号旗的绿翅膀
和萦绕于孤松鬓角的忧思般的山岚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蜓着
列车
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
不能看书 不能作画 不能织毛线
甚至找不到一粒星星的棋子
布进迷失了经纬的棋盘
空的 又是生命的空白
黑暗 又是希望的黑暗
仿佛突然回到 火的根芽
从燧石中苏生以前的历史
仿佛突然跌进 迷乱的岁月
同伴们灵魂的深渊
多臂的风扇
急躁地挥动着 挥动着
驱不散梦魇似的担忧和预感
隧道里
车轮和铁轨
碰撞出刺耳的忧烦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痛苦与欢乐之间
多想看一眼新架的油井和杆塔
小鸟的音符
高低在电缆的五线谱上
把春的乐思 谱进光明与自然
多想光一般地追回
车窗里撒出的传单和青春
晚上的列车
错过在站台上的号旗和手绢
多想风一般地穿过山的围截
谷地落叶般层积的岁月和箕形的蓝天
让深壑挤窄的胸脯
走向黄河上初张的帆篷
让隧洞幽闭的年代
永远属于断碑和古冢
让思想
象扇形的道路
自由地伸向八百里秦川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不是没有过灿烂的经历
不是所有的光明
都属于飞逝的瞬间
为了联结被阻隔 被遗忘的村落
被阻隔 被遗忘的心
为了地平线一样辽远的目标
为了每个站台都成为史诗的一个句点
铁路旋升着
一层层的桥梁隧洞
从山麓蜿蜒而上
分出光明的层次
阳光从山顶的树冠筛落
射进昏暗的窗口
烘暖过潮湿的灵魂
点燃过冰结的血液
一次
又一次
激溅起幸福的泪泉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死灭与新生之间
隧洞象黑洞洞的网口
一个接一个
向希望逼来 逼来
映入瞳孔的蓝天破碎了
象迸裂的蓝玻璃
象惊飞的鸽群 哀鸣四散
然而 没有一颗心
眷顾于空谷间短促的明媚
没有一个人
迟疑或停留在网口之前
嬉闹的孩子 偎紧母亲的胸脯
向黑暗惶惑地睁大双眼
白发老人放下车窗
思绪的浓云间 划过皱纹的闪电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邪恶与正义之间
鹰一般盘旋而上
又蛇似地滑进溪谷 滑进急弯
黑暗与光明
从车窗的日历册上
斑斑驳驳地掠过 掠过
掠过现实和回忆 生和死
伟大的荣耀和血腥的耻辱
生命
起落在历史的黑键和白键上
轰鸣起沉郁而辉煌的人的旋律。
黎明和黄昏 从车轮
走向宇宙的两极 走向永恒和无限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着
列车
穿行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希望和失望
交替地折磨着每一个旅客
每一次期待
都象死亡一样漫长
每一次喜悦
却似幽会一般短暂
在窒闷的缄默与期待中
心和每一声悲壮的汽笛
却呐喊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既然没有一条重复的隧道
就绝没有一次重复的黑暗
……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那使院子早早暗下来的墙头,
几只鸽子惊慌飞走。
胆怯的孩子把弄脏的小脸
偷偷地藏在房后。
平时总是在这里转悠的狗,
这会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一群红色的鸡满院子扑腾,
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眼看着葡萄掉在地上,
血在落叶中间流。
这真是个想安宁也不能安宁的日子,
这是在我家失去阳光的时候。
……
1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在这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
放开我!
2
太阳落了。
黑夜爬了上来,
放肆地掠夺。
这田野将要毁灭,
人
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3
太阳落了。
她似乎提醒着:
你不会再看到我。
4
我是这样的憔悴,
黄种人?
我又是这样的爱!
爱你的时候,
充满着强烈的要求。
5
太阳落了。
你不会再看到我!
6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黑暗是怎样地在你身上掠夺,
怎样?
你好象全不知道。
但是,
这正义的声音强烈地回荡着:
放开我!
1973年
……
1
醒来。
是你孤零零的脑袋。
夜深了,
风还在街上
象个迷路的孩子一样
东奔西撞。
2
街,
被折磨得
软弱无力地躺着。
那流着唾液的大黑猫,
饥饿地哭叫。
3
这城市疼痛得东倒西歪,
在黑夜中显得苍白。
4
沉睡的天,
你的头发被深夜揉得零乱。
我被你搅得,
彻底不眠。
也许是梦,
猜透了我的心情,
才来替我抒情。
啊,那被你欺骗着的
数不清的眼睛。
5
当天空中
垂下了一缕阳光柔软的头发,
城市
浸透着东方的豪华。
6
人们在互相追逐,
给后代留下了颜色。
孩子们从阳光里归来
给母亲带回爱。
7
啊,城市,
你这东方的孩子。
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
你寻找着粮食。
8
这多病的孩子对着你出神,
太阳的七弦琴。
你却映出了她这样瘦弱的身影。
9
城市啊,
面对着饥饿的孩子的眼睛,
你却如此冰冷,
如此无情。
10
黑夜,
总不愿意把我放过。
它露着绿色的单眼睛。
可是,
你什么也不对我说。
夜深了,这天空似乎倾斜,
我便安慰我:
欢乐吧!
欢乐是人人都会有的!
1972年
……
 扫码关注小程序
微信搜索 Xuebody在线
扫码关注小程序
微信搜索 Xuebody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