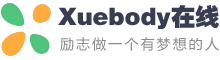曾经想过
曾经想过把彼此的灵魂分开,
但穆契卡卜和扎克萨这两个名字
就像提琴的泣诉
震撼着忧伤的琴弦。
我爱那些名字就像我爱你,
就像你就是它们。
毫无希望地,我爱着你;
并且因思爱成病。
像暗护群星的夜晚,
像哮喘撕开的纱布,
当你袒露双肩,
连楼梯也在颤栗。
那是谁犹豫不决的耳语?
我的?不,肯定是你的。
它们自你的唇间飞出,
像烈酒迅速气化的液滴。
一种思想平静地展现。
它无可挑剔,宛如一声叹息。
它像海岬一样突入夜色,
被月光从三面点亮。
1917
转译自Mark Rudman 英译本。
……